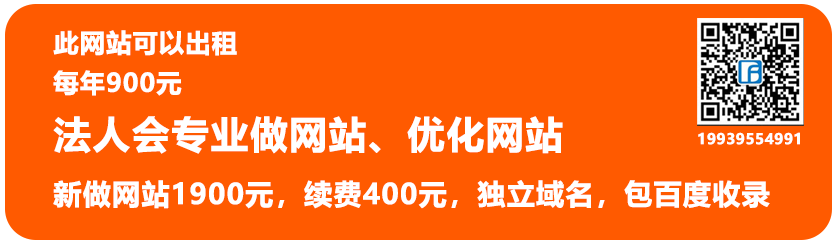敦煌往昔
敦煌往昔
发布日期:2017年03月02日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朋友圈
如果说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天平之甍》写尽了如同百花盛开的大唐中心,那么《敦煌》则道出了流离凋敝的宋代边陲。 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这段叙述,构成了井上靖故事的核心。宋仁宗天圣年间,书生赵行德因为睡觉错过殿试,无意之间又救了一名西夏女子的命,女子给他一块西夏文的布作为报答。赵行德借机游历西域,结果卷入战乱,成为一名西夏士兵,在战争中救了甘州回鹘郡主的命。赵行德因为公务要返回西夏都城,将女子托付给自己的上司朱王礼,两人相约一年后再会,等一年半后赵行德赶到时候,回鹘女子已归西夏王储李元昊,见面后女子以死明志,赵行德转向翻译佛经寻求慰藉。
西夏在河西地区攻城略地之时,朱王礼和赵行德决定杀死李元昊为回鹘女子报仇。瓜州和沙州陷入战火,为了保护佛教典籍,赵行德设法将其藏于敦煌,八百年后方重见天日。
文明竞争是残酷的,而文明又是娇弱的,即使西方文明的渊薮希腊罗马,也是几经易手,最终托体基督教以及蛮族,得以隐约存在。在《敦煌》中,杀戮与战乱是常态,经典的传承则是偶然,其发现也是如此。

《敦煌》
(日)井上靖/著 刘慕沙/译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更为著名的称呼是王道士。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又转卖给西人的故事,大家或许都知道,也曾经散文家任意书写变形,在各种耳熟能详的情节与批判背后,其实遗漏了王道士个体努力,他曾经期待努力使藏经洞得到地方官吏重视而未得,真实的其人其事,都成为未解的过去了。
井上靖在《敦煌》书中也提到这个被无数人鄙视的人,但并没有给予廉价评定与抒情。只说他 呆坐了一辈子 ,偶然之间,发现了敦煌藏宝库。乱世之中的地方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他将其中一些文物卖给了外国探险家斯坦因等人,剩下的终于引发了北京的重视,敦煌藏宝库随之再次一空。动乱的时代与个人的转折之中,王道士是一个微茫的象征。人们争辩这个故事中的是非,但是或许那时甚至直到今天,它都是一个 是 少于 非 或者没有 是 的故事。照片上的王道士看起来矮小木然,和当时多数照片中的人一样。确实,王道士不明白敦煌的价值,地方官员不明白,当时的人不明白,其实买走敦煌典籍的斯坦因等何尝完全明白。
井上靖在《敦煌》中静静地写了一句话作为结尾, 又过了好多年,人们才明白,不仅止于东方学,这些经典竞是足以使世界文化史的每个研究领域都发生改变的珍宝。
赵行德来到西域之后,遇到说话的人,一问哪里人,总是招来一顿爆打,即使遇到尉迟也是一般,一问来历就被吊打。那是民族杂居的时代,有冲突,却也更世界主义。
这既是写出西域的莽荒,也是时代的变化。赵行德的年代,唐之灿烂已经归于尘埃,从晚唐到五代十国,几乎是最为分裂的时代,其中藩镇林立,即使到宋朝之后,在河西等地仍旧存在各路势力。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个体和文明,都不可以盛世或者今日框架来衡量。
《天平之甍》故事发生在文明昌明时代,而其中鉴真东渡的艰辛,尚且传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敦煌》则是更虚无,在一望无垠的边陲地带,城池、战争、王朝都转瞬而去,个体却要固守每个当下,无论意外从军的赵行德还是王孙之后尉迟光,他们首先要面对是无处不在的生存问题。《敦煌》中人物多次处于战乱,归根结底无处可去,回鹘、吐蕃、回人、西夏等等,无处不在的冲突,无处不在的战乱。
《敦煌》中出现的沙州曹氏,是一段差点被忘记的历史。
书中提到曹氏末代两兄弟,一位是弟弟曹延惠,虔心礼佛,率众向西夏投降,一位是沙州节度使曹贤顺,沙州城破之日,与西夏李元昊战斗而亡,成功逃亡的延惠,亦投火而死,两位兄弟同日而亡。
此节引用了曹氏家传, 方丈室内,化尽十万。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檐飞五采,动户迎风 。其实这个曹氏家传,不少是关于归义军的记载。归义军是唐宋之际战乱的独特产物,诞生于晚唐的潮州地方势力,由名将张议潮建立,后由曹氏接替,其势力存续两百余年。期间,归义军不同时期接受唐宋册封,名义上是节度使,其实完全是地方势力,在当时各方势力之中苦心经营。
归义军和吐蕃之间反复大战,曾经挫败吐蕃对沙州多年统治,和各地回鹘之间也是且战且和。对应《敦煌》故事中的叙述,一说回鹘势力后期摆脱归义军控制,甚至是抗击西夏的主要势力,甘州城破之日赵行德才有机会救下甘州郡主。《敦煌》中称臣的是弟弟,哥哥阵亡,两人忌日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对应真实历史,一说归义军的末代人物哥哥曹贤顺在景佑三年归义军灭亡之日以千骑投降西夏。
曹贤顺气度不凡,有不屈意志,有汉家威仪,被武将朱王礼称为武士, 不是极优秀,就是很愚蠢 。他统帅甘州二十余年,自有气度, 看来曹氏即将亡于我曹贤顺这一代,这也无可奈何。相传古时,这里一度长期由吐蕃统治,汉人平时不得不着番服。只有在节祭之日穿汉服仰天哀恸。想必历史又要重演了。可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永远征服这块土地,正如吐蕃最后离去一样,西夏迟早也会离开。到时,你我的子孙将会留下来,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因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汉人之魂,要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多得多。告诉你,此地是汉土。
长兄曹贤顺关注汉土得失荣誉,最后应战西夏时也不失沉着勇猛。弟弟曹延惠看似柔弱,却有先知气度,他也为保护经典做出了贡献。多少源于他的超然,比起政权更迭他更在意保全宗教,所以为了保全寺庙宗教一早就投降西夏。然而他对于时局判断一直不失清晰,对于佛教经典的价值与关切也矢志不渝,而曹氏家传的保存,多少也是依赖他。
两人谁的价值更大,谁更值得敬佩,其实很难判断,也是基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唐宋之际河西地区,充满了战争、多民族角力以及文明的断裂,大家预先看好的角色往往在现实之中折戟沉沙,在评判历史时候,尽量不带立场的进入可能能够离历史真相更近。
几乎转瞬之间,百年基业的曹氏灭门,沙州灰烬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保存?
赵行德偶然路过寺庙,看到僧人们不肯离去,他们在选择佛经,带着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自己没读的很多,好的经典又太多。此情此景,赵行德灵光一闪, 或许唯独还有经典可以幸存。对,不能挽救别的东西,或许可以挽救那些经典。
赵行德还有一段内心独白,这大概是井上靖对于经典的见地, 财宝、生命、权力,倶属个人所有,经典则不同,不属于任何人。只要不被烧毁,搁在那里就行了,谁也抢不走,谁也没法将之据为己有。单是完好存放在那儿,便已经是价值连城。
全书由赵行德贯穿,但是他其实并没一般主角的高大全形象,作为主角的光芒也被掩埋在无穷无尽的战场与打斗中。赵行德是一个被动的人,被动地错过殿试,被动地加入西夏军队,被动地错过与回鹘郡主的一年之期,甚至最终加入杀死李元昊的机会也是被动的复仇。他一生主动的三次,其实都是基于偶然的外力推动,因为偶遇凶残的男子伤害西夏女子而救下后者,因此被分配攻入甘州烽火台,在战乱中不得不救下甘州郡主,再因为沙州大战尉迟光敦促藏宝而动念保存经典。
赵行德的行为,多少带有佛教的出世,是动乱年代无所适从无根可归的人一种应对与自我保护。全书迷漫着一种被动感觉,其实应和着井上靖以悲观为底色的世界观。《敦煌》在井上靖的著作中显然比其他书更出名。据说无数人拿着这本书去敦煌。据说作者写的时候全然没有来过敦煌,最后却发现和他想象的一样。井上靖记者出身,终成文豪,不是靠脚,主要靠脑。
原文浑宏,译文典雅,有种哀而不伤的含蓄壮美。借朋友说法,汉文化如同书中的回鹘女子陷于迷失,而井上靖挖掘之功,犹如主角赵行德之救该女子于水火。悲哀的是,赵行德和她终究是萍水相逢又散去,结果难有佳话,倒也类似现状的遗憾与残缺。隔了八百多年,井上靖写敦煌的心情,大概亦如赵行德日后怀念甘州郡主,不是对人的具体思念,而是一种超越的类宗教体验, 回想起回鹘女子的往事时,行德就会感觉到身体中充满了一种崇高的静谧,它既不是对故人的爱恋,又不是对冤魂的怜悯,而是一种对纯粹完美事物的赞叹。
敦煌地名由来,也有讲究。 敦煌 据说最早见于《史记 大宛列传》,汉朝正式设敦煌郡,《汉书》中说 敦,大也,煌,盛也。 如果要理解敦煌,或许应该从大与盛的开始。按照剑桥历史学者看法,隋唐开始,周边多半还是部落文化,但是到了晚唐,周边已经被稳定国家包围。这种情况下思考历史,其实更应该超越民族观点,正如诺贝尔奖作家奈保尔说,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改变看待其历史的方式,就没有基本也没法写作。
看历史,往往会被传统框架所限定,即使将放在全球历史来看,也往往是将与西方做出对比,重点也局限于明清以来的交流。其实,如果将地图移动,以区域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那么文明是在黄河文明与中亚文明激荡之下的产物,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构成文明盛衰秘线,草原的作用不容忽视。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为例,不谈其政治文明建制的成就,单单就其存在的时间看,其历史跨度仅次于汉唐。南宋往往被视为正统,事实上若论版图,辽国金国更应被视为代表。《敦煌》中有一句话,世上一切皆因缘。当太多的变动,太多的离别,太多的伤害,我们不能接受之时,就将其看做一种业,一种承受。我们的祖先和族人,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活下去,他们的血液,仍旧在我们的身体里游走。








![河南三农物流中心[官网] - 河南物流中心 河南三农物流中心[官网] - 河南物流中心](http://cdn6.bao-fang.com/0013/images/wenhua_gg.jpg)